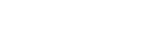冬天吃的菜 , 有乌青菜、冻豆腐、咸菜汤 。 乌青菜塌棵 , 平贴地面 , 江南谓之“塌苦菜” , 此菜味微苦 。 我的祖母在后园辟小片地 , 种乌青菜 , 经霜 , 菜叶边缘作紫红色 , 味道苦中泛甜 。 乌青菜与“蟹油”同煮 , 滋味难比 。 “蟹油”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 , 加猪油“炼”成的 , 放在大海碗里 , 凝成蟹冻 , 久贮不坏 , 可吃一冬 。 豆腐冻后 , 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 。 化开 , 切小块 , 与鲜肉、咸肉、牛肉、海米或咸菜同煮 , 无不佳 。 冻豆腐宜放辣椒、青蒜 。 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 , 只有“青菜” 。 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 , 美其名曰“黄芽菜” , 很贵 。 “青菜”似油菜而大 , 高二尺 , 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, 家家都吃的菜 。 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 。 阴天下雪 , 喝咸菜汤 。
冬天的游戏:踢毽子 , 抓子儿 , 下“逍遥” 。 “逍遥”是在一张正方的白纸上 , 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 , 两道之间印出八仙、马、兔子、鲤鱼、虾……;每样都是两个 , 错落排列 , 不依次序 。 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 , 掷骰子 , 如果骰子是五点 , 自“起马”处数起 , 向前走五步 , 是兔子 , 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个兔子 , 以子儿押在上面 。 下一轮开始 , 自里圈兔子处数起 , 如是六点 , 进六步 , 也许是铁拐李 , 就寻另一个铁拐李 , 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 。 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 , 则到外圈去找 , 退回来 。 点数够了 , 子儿能进终点(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 , 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) , 就算赢了 。 次后进入的为“二家”、“三家” 。 “逍遥”两个人玩也可以 , 三个四个人玩也可以 。 不知道为什么叫做“逍遥” 。
早起一睁眼 , 窗户纸上亮晃晃的 , 下雪了!雪天 , 到后园去折腊梅花、天竺果 。 明黄色的腊梅、鲜红的天竺果 , 白雪 , 生意盎然 。 腊梅开得很长 , 天竺果尤为耐久 , 插在胆瓶里 , 可经半个月 。
舂粉子 。 有一家邻居 , 有一架碓 。 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 , 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 。 碓屋很小 , 除了一架碓 , 只有一些筛子、箩 。 踩碓很好玩 , 用脚一踏 , 吱扭一声 , 碓嘴扬了起来 , 嘭的一声 , 落在碓窝里 。 粉子舂好了 , 可以蒸糕 , 做“年烧饼”(糯米粉为蒂 , 包豆沙白糖 , 作为饼 , 在锅里烙熟) , 搓圆子(即汤团) 。 舂粉子 , 就快过年了 。
秋雨打着她们的脸 。 一堆堆深灰色的迷云 , 低低地压着大地 。 已经是深秋了 , 森林里那一望无际的林木都已光秃 , 老树阴郁地站着 , 让褐色的苔掩住它身上的皱纹 。 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衣裳 , 它们只好枯秃地站在那里 。
秋天带着落叶的声音来了 , 早晨像露珠一样新鲜 。 天空发出柔和的光辉 , 澄清又缥缈 , 使人想听见一阵高飞的云雀的歌唱 , 正如望着碧海想着见一片白帆 。 夕阳是时间的翅膀 , 当它飞遁时有一刹那极其绚烂的展开 。 于是薄暮 。
晚秋底澄清的天 , 像一望无际的平静的碧海;强烈的白光在空中跳动着 , 宛如海面泛起的微波;山脚下片片的高粱时时摇曳着丰满的穗头 , 好似波动着的红水;而衰黄了的叶片却给田野着上了凋敝的颜色 。
多明媚的秋天哪 , 这里 , 再也不是焦土和灰烬 , 这是千万座山风都披着红毯的旺盛的国土 。 那满身嵌着弹皮的红松 , 仍然活着 , 傲立在高高的山岩上 , 山谷中汽笛欢腾 , 白望在稻田里缓缓飞翔 。
当峭厉的西风把天空刷得愈加高远的时候;当充满希望的孩子望断了最后一只南飞雁的时候;当辽阔的大野无边的青草被摇曳得株株枯黄的时候—一当在这个时候 , 便是秋了 , 便是树木落叶的季节了 。
特别声明: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,仅供参考,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。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。